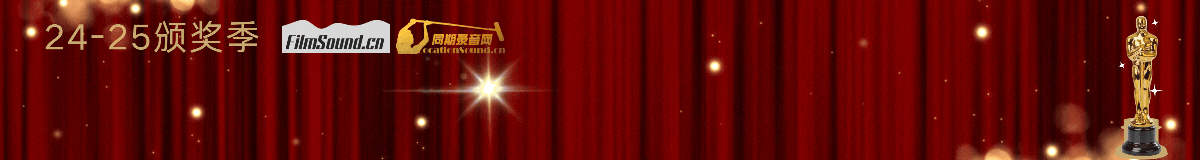促进中国同期录音发展的录音师——桥本文雄

30年前,一部中日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曾经风靡中国。这部由孙道临、三国连太郎主演,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的经典影片,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主人公的原型——围棋大师吴清源的名字,也斩获了诸多奖项。在大家津津乐道的同时,也许人们并不知道,这部影片对中日两国的电影录音技术方面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日本著名的录音师桥本文雄。本期是日本影视录音师系列的第三篇,还没看过前两篇的小伙伴请点击链接:编织自然的声音 录音师铃木肇、支持宫崎骏和押井守的声音总监——若林和弘

桥本文雄(1928—2012),1946年作为录音助手进入大映公司京都摄影所录音部。1954年来到日活(制片公司),在西河克巳导演的电影《以一切活着的人的名义》作为录音师出道。从那时起,他参与了由川岛雄三、井上梅次、中平康、今村昌平导演的日活动作片,以及石原裕次郎主演的电影,为 “日活的声音 “奠定了基础。担任电影录音的作品总共有274部。
Q:您是怎么进入电影行业的?
H:说起来,我也算是阴差阳错才进入了电影录音这个行业。我当初读的是大阪专门学校(即现在的近畿大学),原本想着大学毕业以后就去满洲(二战时日本扶持的所谓“满洲国”)矿山的钢铁厂工作,不多久日本就战败了,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工作好。当时舅舅在大映京都摄影所做制作主任,而那时候的摄影所并不公开招人,很多都是有亲戚朋友的连带关系。由于我在学校里学习也不是很优秀,于是舅舅就来问愿不愿意退学去摄影所做录音助手。虽然不十分情愿,但因为是亲戚推荐的,所以就去参加了考试。没想到,来到现场后我觉得整个过程十分有趣,考试后也幸运地被录取了。
Q:日活公司的黄金时代是怎样的? 以一切活着的人的名义 海报 H:当时真的是不得了呀,只是出任了一部片子的录音助理后,在27岁就能以录音师的身份出道并在西河克巳导演的电影中担任录音师的正职。而且当时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汽车接送的,如果去到大阪以外比较远的拍摄现场还会坐飞机去,工资也是当时大学毕业生的10倍以上。对于当时的助手来说,早日成为录音师才是最大的目标。
Q:当时的录音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
H:当时在公司拍摄的时候拍摄和录音是一起进行的(光学录音),外景拍摄的时候声音是后期录制。录音部包括录音师、负责卷胶片的助手和负责架设麦克风的助手。当时负责打场记板的也是录音部里面最年轻的助手。

录音室设置在摄影棚中一个单独的屋子里面,从那里把线材拉到摄影棚里面,当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需要同时按下蜂鸣器。然后,摄影棚通过电话听到蜂鸣器的声音后,再打场记板并开始拍摄。当时的拍摄工作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了,再往后就是使用磁带录音和NAGRA录音机了。
Q:日活公司的工作气氛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日活聚集了一批从松竹公司、大映公司、新东宝公司等电影摄制公司来的(也包括我),对于拍摄电影很积极也很有想法的人。大家想到有趣的想法也会马上用到电影制作中,比如说在拍摄《猪与军舰》时,我们想拍摄500只猪奔跑的大场面。但是拍摄时它们根本不跑,所以担任副导演的浦山桐郎穿着黑色的学生服在猪群里面四肢并用的追赶它们让它们跑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

Q:听说您也参加过中日合资电影的拍摄,具体是怎样的呢?
H:在北京拍摄中日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时,我认识了录音主任吕宪昌和左山(佐佐木勇吉)。他们都在“满映摄影所”(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过,左山的日语也很好。助手也是两个中国人、两个日本人这样安排的,录音部的大家关系都特别融洽。吕宪昌还表示要按照日本的标准工作。比如,一般来说中国的拍摄现场着急时也不会有人跑起来赶路,只有我们的录音部门包括助手都是小跑着赶路的。

吕宪昌

左山
我在新年和圣诞节的时候也经常能收到他们(中国工作人员)发来的贺卡,还称呼我为“老师”。当我得知,拍摄时担任助手的年轻人小李(李伯江)后来还获得了金鸡奖的最佳录音奖时,我很欣慰。

电影《云南故事》获得第14届金鸡百花奖 最佳录音
Q:都说您影响了中国的录音技术,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H:当时,中国的录音技术落后,没有同期录音的技术。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有20多种不同的方言。因此,即使用北京的普通话拍摄对白,也必须把它转换成当地的方言,所以同期录音的意义不大,也不受重视。但是我坚持的理由是,如果想录到好的声音,至少也要在现场设置这套设备录音。在之后的试映会上播放使用同期录音的片段时,每个人都很惊讶和高兴。
我在中国宣传电影《火红的第五乐章》时,受到吕宪昌等中国最好的技师的邀请,在中国开办了一个录音技术的研究班,当时从中国各地电影制片厂的约30名录音技师赶来参加,学习了日本的先进录音技术。
Q:录音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桥本文雄在拍摄现场
H:我认为是把重点放在声音设计上,因为声音的高潮其实就是电影的高潮,虽然这么说是有一些片面的。无论 “画面”有多美,仅此一点还不足以让它成为一整部电影的高潮。画面是很难将情感延伸到画框之外的地方,但这正是声音所擅长的。
敦煌 日本预告片
例如在电影《敦煌》中,几千匹马奔跑的声音在一瞬间安静下来,在观众的注意力被吸引之后。紧跟着一句“前进!”的呼喊声与音乐同时响起,一下子就把这个场景中骑兵冲锋就像地震一样的震撼表现出来了。原作者井上靖看了以后说这才是能代表《敦煌》的声音。

敦煌 剧照
如今电影摄制中的各种环节都被数字化所取代,声音的要素跟着增多,制作也变的更复杂。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和把握整体声音设计的工作原则是没有改变的。虽然我有时也会想;在某个镜头或某场戏中,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就可以了不用修改了呢?但是从电影的整体来看,我还是会做一些修改甚至重新录音。所以保持电影的整体风格是一直以来我认为的最重要的事。
这篇文章让我们见证了国内外电影录音的发展和相互交流,更显弥足珍贵。如今,桥本文雄虽已去世,但他留下的无数经典作品都作为宝贵的文化财富被保存下来,而他对日本、对中国的电影录音所作的贡献也是令人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