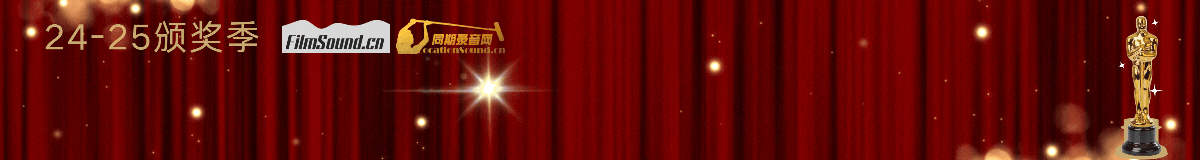《长江图》中的声音制作——制片人王彧独家专访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创作的多方面系统的探讨一部好的电影声音作品——在去年,《长江图》的声音制作获得了金马奖最佳音效奖,这其中不乏导演,制片,声音设计师,同期录音师,拟音师们对声音的重视和付出。本次我们将以连载的形式,多位创作者的视角,走到幕后并共同探讨一部好的声音作品是如何缔造出来的,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能有更多影视部门的老师可以看到。本期是系列中的第三期,我们请到的是《长江图》的制片人王彧老师。

王彧、贾樟柯
所以我对于声音在电影中作用,它的视角和效果可能别的制片人的理解不太一样。我对于电影声音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认为中国电影,大部分对于声音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不管是从预算还是周期以及从声画配合还是从导演的角度以及后期制作上大家对声音并不是特别重视。

王超、王彧
对电影声音而言它其实需要一个认知的过程,包括大家在观影的过程中对于声音作用的认知远没有画面的作用来得强烈。声音的创作和声音的作用需要录音师和导演来共同的架构。
从我的角度来讲,电影声音是为画面提供延展空间的,它为感官能直接看到的东西做二次升华,好的声音是沉浸式的,是包裹在画面里的感觉,它不需要跳出来让你特别的注意到,除非某些段落可以特别通过声音来表现其气氛。大部分的情况声音其实是为了让观众包裹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让人感到舒服。

王彧、李屏宾

我毕竟没有跟全程的前期,但是我在与录音师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都认为《长江图》前期收声的困难在于,很多的场景都在船上,在船上的收声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江上的转场也是比较困难的。
还有比如说中间有一场戏是男演员一直爬那个万寿塔去找女演员的那场戏,这个场景中录音师在关于客观声音还是主观声音上面花了很多精力,声音有塔内塔外的切换。另外,这个塔有一个特殊的声学结构,所以对于特殊场景录音师们还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前期录音师房涛,后期录音师房涛、郝智禹都是我的同学。他们对于《长江图》的整体空间创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观。
 还有就是过三峡大坝闸口的那场戏,那种在隧道里的感觉几乎让人濒临崩溃的边缘,我在拍《三峡好人》和《长江图》时都经过了这个闸口。录音师当时采用了很多金属摩擦的声音和大的混响,还有一些环境噪声,整个空间的临场感特别强烈,这场戏也得到了金马评委的高度认可。
还有就是过三峡大坝闸口的那场戏,那种在隧道里的感觉几乎让人濒临崩溃的边缘,我在拍《三峡好人》和《长江图》时都经过了这个闸口。录音师当时采用了很多金属摩擦的声音和大的混响,还有一些环境噪声,整个空间的临场感特别强烈,这场戏也得到了金马评委的高度认可。
《长江图》其实是把一些年代感抽离了,它并没有那么多年代的符号,除了一些特指的音响和音效,录音师需要规避很多现代,当代的声音,所以《长江图》都是录音师们利用想象力创造的空间。
很多细节,包括船的发动机的“突突”声音其实是用了很多条的音响来拼贴出的声音,发动机的声音也会随着画面和剧情的转折,不同的节奏和气氛,完成不同的叙事功能。如果是完全是一个枯燥的马达声的话观众会显得十分的疲惫,所以这点录音师们做了很多的设计。

还有就是音乐和电影声音的关系,其实音乐也是构成整个电影声音,空间音响的一部分。这部影片中的音乐大部分都是采用海外的版权音乐。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与画面气质,音响空间,场景声音都十分契合的音乐。原来是希望能够在国内找人来写,但是很难找到类似感觉的作曲。

前期工作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白要收清晰,第二就是环境声和群杂,第三是特殊效果声。这些构成了后期的素材,而且这些素材都需要有清楚的标注。再有就是要与导演对电影进行空间上的讨论,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把前期的工作做的更好。
对于后期的录音师或者是混录师而言,在漫长的后期工作的过程中的有效沟通是最重要的,大部分的导演其实他们都懂声音,但是对于如何实现场景空间并没有完善的概念,比如像《长江图》,前期资料是相对充足的,后期做特殊场景声音资料花费了很多精力。不过郝智禹和房涛与导演的沟通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画面和声音这两个创作环节是分开的,在画面的基础上导演需要展示的是什么空间,都需要沟通交流。也许它只是一个小景别,但是他需要的是一个大环境背景,如果单靠画面传达那没有办法把画外的空间补充进来。

后期的工作有几个方面需要重视,第一是完整的传达影片气质,第二是画外的延展空间,第三是特殊场景音响的控制,我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表现。大家经常会听到有些电影的声音过于突出,一部90分钟的电影如果声音太突出耳朵会不舒服。声音和音乐一样,要有起承转合,有节奏和强弱表现。电影声音是一个音响的概念,对白,音乐,环境声,效果声加在一起是有韵律的表现。
对于国内来讲,有些影院的环放条件会比较差,有些影院出现音量不够,环绕声有问题,甚至一些喇叭都不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遗憾吧。我们在海外电影节或者正式放映之前都会仔细调试音量,检查它的环绕。
我们也期待国内的影院从硬件设施到设备维护都能有一些技术标准的提升。也许未来我们会请录音师和导演到标准影院对《长江图》做一些声音的解析。感谢对《长江图》的支持,多谢。


《长江图》声音制作独家系列专访 声音指导房涛、郝智禹(上) |(下) |同期录音师李硕专访 |导演杨超(上)| (下)|制片人王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