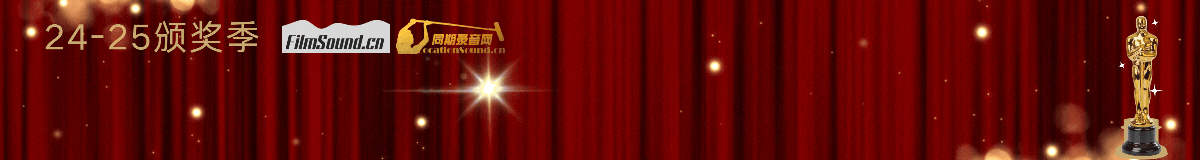《长江图》中的声音制作——同期录音师李硕独家专访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创作的多方面系统的探讨一部好的电影声音作品——在去年,《长江图》的声音制作获得了金马奖最佳音效奖,这其中不乏导演,制片,声音设计师,同期录音师,拟音师们对声音的重视和付出。本次我们将以连载的形式,多位创作者的视角,走到幕后并共同探讨一部好的声音作品是如何缔造出来的,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能有更多影视部门的老师可以看到。本期是系列中的第二期,我们请到的是《长江图》的同期录音师李硕老师。

我叫李硕,生于北京,1997-2001,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本科。


拍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或者那个)拍了有什么用,但也就拍了。

可以说一个细节,男主演秦昊(他在出演《长江图》之前,已经是业内知名的艺术电影的演员),在开机不久有一次我给他装无线话筒的时候问我:“这船的发动机这么大声,同期还能用么?”我说:“从信噪比上讲应该是可以用的。”balabala一些理由,然后他马上接着说,这戏可没法儿配啊,你可录好了,我可不配音!
当然他说这个话,也许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我实际上很喜欢在这个特定的电影,对于高淳这个角色,他的这个态度。大量的台词能力不过关的明星(不太能用“演员”这个词),在电影中的出现,是现在的电影很多需要后期配音的主要原因之一。像秦昊这样对自己的台词有信心,对自己现场表演有信心,不想因为技术原因后期配音而损失角色塑造的演员,是难得的。我作为现场录音师,喜欢这样的演员。同期录音师大概都是希望自己录的同期声能够尽量多的用在成片里,如果演员也是这么想的,那是再好不过了。

跟我们很多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说,很多导演,监制,老板也包括在其中)对同期录音缺乏尊重相比(至于要让大家懂一些电影声音的基本知识,更是奢求),在《长江图》里遇到的比如我们那艘破旧不堪的货船的吵闹的发动机啊,不得不挪来挪去尽量减少对同期录音干扰的小型汽油发电机,都算不上困难。
比如,在我们的船通过三峡五级船闸的时候,我拿着手持的录音机在船头附近录音,同样也在附近的其他同事,大部分在我的提醒下(但,看到录音师手里拿着亮着红灯的录音机在录那么珍贵的声音资料呢,自觉的保持安静难道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影工作者应该具有的专业素质么?),大家都可以保持安静,摄影部门一个小朋友依然说说笑笑,在我再次呵斥他安静的时候,他还大喊大叫的质疑我。这其实是我们很多电影,拍摄时候的现状,我除了苦笑,其实没有其它办法。
我的看法,电影同期录音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就是这类不专业,不敬业造成的。

(以下和本片无关,纯属发牢骚:
再举个例子,在胶片电影时期,摄影机本身的构造问题,马达声音在某些安静的内景的时候会影响同期声,很多摄影师自己听到了会主动让助理拿衣服或者毯子临时的包一下,多多少少会有些效果。但到了数字摄影机时代,不少机器组的小朋友,就是不愿意把散热风扇调到REC LOW的模式。我相信不少同期录音师都会有跟我相同的和不专业的同事斗智斗勇的经历。)

另外,杨超导演是个好人。在我跟他们去看景的时候,那条船是没有地方给那么多人睡觉的,制片临时在货舱里用三合板搭了个棚子,给大家打地铺睡觉,但因为用的劣质板材和胶水,那个棚子里甲醛味道刺鼻,我下去几秒钟便流了眼泪。我当然拒绝在这样有毒的环境里过夜睡觉,就自己在甲板上睡在我带的睡袋里。那是十一月初的长江,间或还飘些小雨,所以,肯定谈不上是个怡人的睡觉环境。但船桥上除了船工的床铺以外,唯一的床位,是给导演的。我没有其他选择。晚上我睡了没多久,被杨超导演推醒了,他知道我为何要睡在这里,所以没有劝我回“有毒的船舱”睡觉,而是说,李硕你去我的床位上睡吧,我可以睡躺椅。我当然得拒绝,说了一些我有很多野外宿营的经验,露天睡睡袋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之类的客气话。
最后,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个助手,万贵鳌和李志国,在拍摄期间的辛苦付出。

《长江图》声音制作独家系列专访 声音指导房涛、郝智禹(上) |(下) |同期录音师李硕专访 |导演杨超(上)| (下)|制片人王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