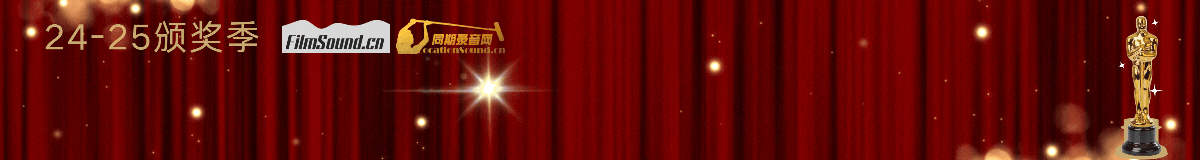巾帼不让须眉—国内女性专业影视声音工作者访谈录(四)

前三期女录音师访谈我们分别请来了龙筱竹老师 | 李敏娜老师 | 田昕老师(点击链接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些工作在电影声音制作一线的女性们,多多转发我们的文章。
本期的女录音师请到的这位老师,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熟悉,但提起她的几部作品包括《前任》系列和电影《何以笙箫默》应该就知道了,她就是声舞者工作室的创始人和声音总监胡靓老师,她同样毕业于“电影人才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走进她,了解她。

第4期
胡靓,2003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参与多部电影、电视剧的同期录音和后期声音制作工作。2009年和电影学院校友共同成立了声舞者工作室,现任声舞者声音工作室的后期总监,参与了工作室大部分项目的声音设计及编辑制作工作。代表作品有:
在录音棚工作中
我是1999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的,大三的时候遇到一个在录音棚实习的机会,算是正式进入这个行业吧,当时主要是做ADR录音和声音编辑。我们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从线性编辑到非线性编辑的变革时代,学校引进了Nuendo工作站,我们每周可以在里面呆一整天做一些电影声音小片段,那是非常幸福的一段时光,就好像在实验室做试验一样。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愿意跟工作站打交道,因为很享受那种自由地做试验的感觉。
我现在主要是做声音设计工作,从前期剧本讨论就参与进来,到整个声音后期和混录完成,这中间每个环节都涉及。
第一次录音是做张建栋导演的电视剧《绝对控制》的ADR录音,那时候我还是个新手,刚熟悉了Pro tools工作站的操作,紧张是肯定的。但是当时的工作氛围非常好,每一个补录段落导演都会先跟演员一起斟酌台词和情绪再进棚录音,不急不躁,大家既认真又很轻松,我有一些小的操作失误也没有任何人催促我,这让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也为以后的录音工作建立起了自信。
第一次现场录音是在管虎导演的电视剧《活着,真好》,做B组录音师 。有一个长镜头的拍摄非常费劲,摄影师肩扛摄像机跟拍演员从客厅走到厨房,在厨房拿完东西转过身上楼,然后再跟上楼。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楼梯口空间非常的小,演员转身上楼的时候,摄影师也得往后退,后面站不下第二个人了,话筒员跟在摄影师身后就没地方站,还好正对楼梯的地方有个壁橱,话筒员可以打开门站里面。可是问题又来了,正常的时候壁橱的门都是关着的,镜头跟进厨房的时候门还得关着,所以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大家先跟进厨房,然后话筒员一手举杆一手推开壁橱的门退进去,等演员上楼的时候再跟出来顺手带上门,这一系列动作还得轻轻地完成,是不是很有难度?话筒员不仅要有力气还得会杂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也是不容易。

与工作室同事们合影
对于录音师来说,可能会有风格上的偏好,但对于每一种声音本身应该都是很敏感的,很难说哪一类声音是好的声音。风格明朗的,层次清晰的,能帮助电影叙事的,能直击观众心理的,甚至噪声利用的合理,都是好声音。我个人很喜欢那种能牵引观众情绪的声音,所有对声音的处理都是希望观众对人物情绪和影片气氛有心理上的感受,而不仅仅是感官的刺激。当你需要放大这种感受时就去强化某些声音元素。我还没获得过声音方面的奖项,说不上成就,但有些作品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比如说电影《我们俩》。影片讲的就是一个话多的孤独老太太和一个话少的活泼少女之间的日常琐事,四季更迭,几乎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小院里,叙述非常朴实,但就是让人觉得情感很真实。声音氛围的营造也随着两人感情的变化,从冷清变得热闹最后又回归到冷清,不煽情却恰到好处。
目前主要做后期工作多一些,所以常用的设备就是Pro tools工作站。
 与来启箴老师合影
与来启箴老师合影
我的偶像很多啊,我非常幸运地跟声音领域的很多大师学习过,受益匪浅。来启箴老师和陶经老师都给过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来老师很风趣,爱钻研和挑战极限,从他那里总能学到些妙招。他是个特别爱工作的人,可以自己一个人关在小棚里研究一天插件的用法,然后在我们干活的时候就忍不住过来传授点小秘诀,是个挺可爱的老师,跟他一起工作让我觉得做声音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陶老师是另外一种风格,他思路非常清晰,对影片的解读很快也很准确,看一遍影片就能找到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捋清声音制作的方向,不得不让人很佩服。
 《何以笙箫默》混录工作照
《何以笙箫默》混录工作照
我现在出前期的机会很少了,但是后期也需要经常加班,特别是到后期混录的时候。我的家人很给力,他们很了解我的这种工作性质,都很支持我。我先生是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他其实挺羡慕我这种工作的,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可以相对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当我很忙的时候他会主动承担起家庭责任。在做电影《何以笙箫默》的时候,由于赶上映档期,制作周期被压缩得非常短,混录的时候每天工作时间很长,需要住在中影。我那时候还在哺乳期,中影混录棚没地方存奶,正好那几天赶上周末了,我先生就带着宝宝也住在中影,每隔几个小时就开车来混录棚找我喂奶,直到混录结束。这对每个职场妈妈来说都是个不容易的阶段,我十分感谢当时剧组各位同事的理解,没有他们的理解,我就很难专心投入工作。对我的家人,我只能是感恩,在我工作比较少的时候多陪陪他们。有了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我觉得工作和家庭还挺好平衡的,当家里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工作就成了一个发泄出口,专注地工作一段时间,世界就又平和了。
 在澳洲旅游
在澳洲旅游
通常工作越紧张就越需要高质量的休息来恢复体力,长时间疲劳工作注意力会下降,影响工作效率。如果需要迅速地从紧张的情绪里出来,我就出去走圈儿,多走几圈就能很快恢复平静,然后再去睡觉。做声音后期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对着工作站干活,很少跟人说话交流,时间长了难免会心情抑郁,我会隔一段时间跟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吃个饭聊聊天,马上又能满血复活啦。偶尔我也做做运动或者出去旅行,这都是很好的放松方式。
 与声音部门小伙伴在《 摆渡人》首映现场
与声音部门小伙伴在《 摆渡人》首映现场
我进校的时候录音系只有一个专业一共就几十个人,系主任黄宴如有一次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录音是很边缘的专业,我们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毕业后发现愿意从事录音工作的同学真的挺少的,现在还留在录音岗位上的就更少了。影视行业比较特殊,需要长期加班和出差,很多人在工作和家庭不能兼顾的时候选择了回归家庭。这样也挺好的,个人选择而已。我之所以能在这个行业里坚持下来,除了家人很给力,还有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吧。从当年懵懵懂懂地报考录音专业到现在工作了十几年,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成长,也很享受工作的乐趣,老师和同行的鼓励也是我工作的动力,我非常庆幸当年选择了这个专业。
我最近在做一个美食类的纪录片,纪录片我做的相对比较少,这次体验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多做一些不同风格的纪录片吧。接下来还有张建栋导演的一部电视剧要开始做后期,另外有部电影会在九月份开机。
 工作中
工作中
录音师是个很孤独的职业,因为在工作的时候眼睛耳朵和手都要同时用到,不能分心干别的事情,所以要耐得住寂寞,学会跟自己较劲。技术的习得可以通过三两年不断练习来达成,艺术感知却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对影片的解读能力会影响声音制作的水平,多看多听多体会吧。再就是注意休息,人在极度疲劳的时候,听觉和理解力都会下降的。
现在没有带新人,我认为跟着老师学习确实能养成好的工作习惯,但是现在师傅带徒弟这种形式很少了吧。主要是习得知识的途径多了容易了,上网一搜就能找到自己想了解的知识。而且知识都是在不断更新的,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我现在很喜欢合作的形式,跟不同的人合作总能学到新的东西,大家对影片的解读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对声音的处理也会有很多自己的心得,这些碰撞都能让我们有更多收获。
 工作中
工作中
我进入这个行业最初的工作模式是,一个声音编辑从开始修对白、ADR录音、贴环境音效到最后的混录完成,编码转光都是要跟下来的,可以说是录音师的后期助理,一部戏下来各个工种都涉及到了,成长很快。现在工艺流程有了很大的变化,声音后期被划分成好几个部门,对个人来说可能成长的速度变慢了,但对行业来说是好事,每个细分部门的业务水平都能更精进,声音的整体制作水平一定是在提高的。我觉得未来影视声音行业会在技术上更专业,声音部门更细分,合作会变得很重要,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就需要有规范的合作模式和标准,这是我们需要开始着手准备的事。

推荐阅读:点击下方图片即可阅读